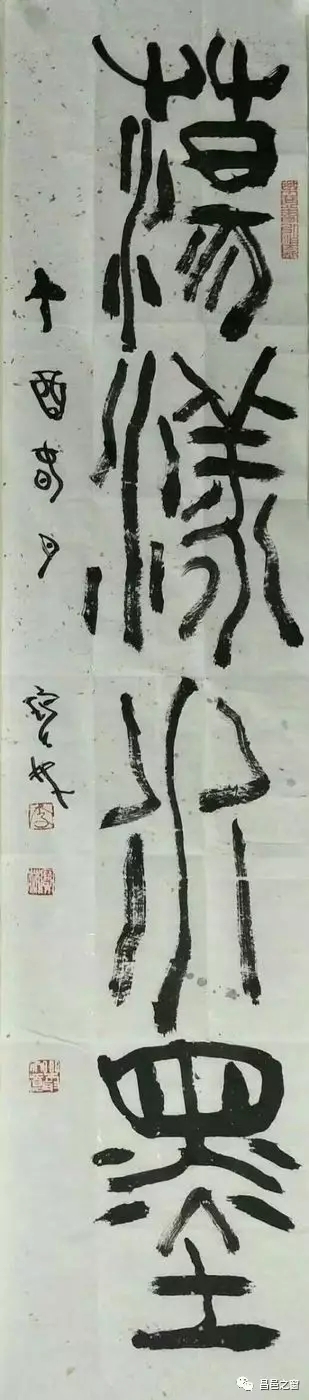张明川与崂山的不解情缘

张明川,著名军旅画家,1962年出生于山东昌邑,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。现为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创作室专职画家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员,中国画学会理事、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作品数十次参加全国、全军重大美术展览,二十多次荣获各种奖项。其中《海天流韵》荣获第十届全国美展特别奖——关山月美术基金奖、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;《灵气郁盘》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,《世纪构建》获纪念建党80周年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(最高奖)、第十届全军美展优秀作品奖,《云山空蒙》获首届全国写意画大展优秀作品奖(最高奖);《盛世风华》获首届全国花鸟画艺术大展优秀作品奖;《云山空灵》、《春酣》分别获2003、2004年全国中国画提名展铜奖和银奖等。先后入选第八届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美展,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全国中国画展,第九届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全军美展,庆祝建党90周年全国美展,心系汶川·全国美术特展,首届金陵百家中国画展,2008全国中国画学术邀请展,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美展,《天山南北》中国美术作品展,首届全国中国画学术展等,出版画集十多种。
青岛崂山的奇峰峻岭,给予了张明川不尽的创作源泉,他一直在凝望崂山,用画家的胸怀拥抱崂山,用手中的画笔展现崂山……

在我心目中,崂山就是一座永远无法窥尽的奇山。它像一本书,一部长篇巨著,内涵深邃而情节丰富;它又像一部交响乐章,时而委婉曲折,宁静舒缓,时而跌宕起伏,气吞天地,荡气回肠。

崂山,看其势,蔚为大观,多有胜绝处,不与众山同。或 崔巍,或嵯峨,或雄浑,或峭拔,或苍润,或明秀,皆为妙观,若能饱观熟玩,混化胸中,皆足为我学之助。 自古以来,道教名山莫不如此。

崂山文化由来已久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咏崂山:“我昔东海上,劳山餐紫霞。亲见安期公,食枣大如瓜。中年谒汉主,不惬还归家。朱颜谢春晖,白发见生涯。所期就金液,飞步登云车。愿随夫子天坛上,闲与仙人扫落花。”。太白此诗《寄王屋山人孟大融》镌刻于崂山梯子石五百级处之巨石上,刻石之诗与《李太白全集》所载相同。

五代刘若拙《入 觐回劳山》诗云:
东来海上访道玄,幸遇一见有仙缘。宋朝天子丹书诏,奉命敕修道宫院。
海角天涯名最胜,秦皇汉武屡敕封。古来游仙知多少,元君老子初相逢。
刘若拙,后唐同光二年(公元924年),自四川来崂山,曾被宋太祖敕封为“华盖真人”。在《宋史·甄栖真传》中,有甄栖真“初访道于牢山(即今之崂山)华盖先生”的记载。

金.刘迎诗云:
君不见二牢山下狮子峰,海波万里家鱼龙。金鸡一唱火轮出,晓色下瞰扶桑宫。槲林叶老霜风急,雪浪如山半空立。贝阙轩腾水伯居,琼瑰喷薄鲛人泣。长白柄光芒寒,一苇去横烟雾间。峰峦百叠破螺早,宫室四面开耗山。。。。。。(刘迎,字无党,东莱人,金代大定十四年(1174年)进士。)
金。朱仲明。《华楼崮》:
群峰鸆H簇华楼,天老人间境界幽。辟谷仙翁发长啸,一声铁笛洞外秋。
(朱仲明,即墨人,举人,曾任即墨县教谕。)
看来,狮子峰、华楼崮早己有此名,由来已久。

元代大诗人、大书画家赵孟頫《咏劳顶》:
山海相依水连天,万里银波云如烟。挥毫绘成天然画,笔到穷处难寻源。
然而,在崂山留下最多足迹和诗文者,莫属邱处机,如:
“烟岚初到上清宫,晓色依稀路径通。才到下方人未食,坐观山海一鸿。云海茫茫不见涯,潮头只见浪翻花。高峰万叠连云秀,一簇围屏是道家。”
“五岳曾经四岳游,群山未必可相俦。只因海角天涯背,不得高名贯九州。陕右名高华岳稀,江南尤物九华奇。鳌山下枕东洋海,秀出山东人不知。”
据说,仅邱处机流传于今世的咏崂山诗就多达数十首。可见崂山历史文化悠久,在古代就名气很大。

谚曰:“黄山归来不看岳,五岳归来不看山。”然而,我走遍三山五岳,仍不减对崂山的特殊之爱。因为崂山之美,没有一座名山可以替代。
我经常考虑,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崂山之美,那就是“奇幻”。

江山无限景,都聚一亭中。

我喜欢崂山,更多是因为它处处皆入画,鸿蒙万象,千变万化,神秘莫测。我对崂山之爱说不清,也道不完。

“见青烟白道而思行,见平川落照而思望,见幽人山客而思居,见岩扃泉石而思游。”崂山之美给我取之不尽的灵感,也常常激起我创作的冲动。

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
写生应该是山水画家常态化的事情。

尽管是冬日之山林,可此时我想到“春深杏花乱”的诗句。
正是因为它的丰富、变化和神秘,也令画家束手无策,无法表现。写生往往就是这样,我们目中所见与艺术表现是千差万别,距离甚远,若要把自己的特殊感受以笔墨形式转换成艺术作品,这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。

岭边树色含风冷,石上泉声带雨秋。

写生是一篇大文章。
画家不是简单的照搬大自然于纸上。画家的任务是创造一种自我的艺术语言,是把目中所见、胸中所思用笔墨方式表现在纸上,这个创作过程,往往是画家最为钟情和享受其中的事情。

我常常选取如水库一寓,村头一角,或山道弯弯、溪水潺湲、疏林野径等等,这些简单、朴素而且随处可见的普通景象作为创作题材,这些寻常景像似乎更加纯朴、亲切和丰富。

“石走山飞气不驯,千峰直作乱麻皴。”崂山之形态常有不可思拟之妙。

山林有异趣,野草入诗香。
相比那些游人较多的名胜景点,我更喜欢去山远地偏的荒郊野岭,这些地方多有野逸之气,山中一草一木皆可入画。
苍茫是崂山最突出的形态美。追求笔墨的苍茫感又是我的偏爱,对此我不厌其烦。清代郑绩有云:意欲苍老,笔重而劲,笔笔从腕力中折出,故曰有生辣气。墨主焦,景宜大,虽一二分合,如天马行空,任情收止(《梦幻居画学简明》)。墨主焦,是其诀窍,读清人此论,深受启发。尤其 崂山的寒冬疏林,莫如用干笔焦墨,最能体现瘦劲挺拔的苍林。这是我的强烈感受。

古人有”聊浮游以逍遥”,但古之文人墨客,能身至崂山者,无非数人而已。
日日溪边林下,坐忘纷乱尘世。在山中写生作画之乐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清人.笪重光《画筌》中载:夫山川气象,以浑为宗;山峦交割,以清为法。清而不薄,厚而不腻,这也是山水画用墨之要,之窍。
所谓“大家在气象”。嗟乎,盖画家胸中气象之境,皆从山川自然中来也。

语云:“造化入笔端,笔端本造化。”此之谓也。

峭壁连空洞,攒风跌翠微。鸟声堪驻马,林色可忘机。

“世之笃论,谓山水有可行者,有可望者,有可游者,有可居者。画凡至此,皆为妙品。(郭熙)”然我观崂山,可行可望可游可居,皆可得矣。

“ 静极却嫌流水闹,闲多反笑野云忙”(唐。韦庄)。
“芳草白云留我住,世间何事得相关”(唐。皎然)。
难怪昔丘处机来到崂山后留恋往返,乐此不疲,从此身居山中修道养生。

这些作品许多都是我在天寒地冻,北风刺面的隆冬时节在山里画的,这时的风景更为苍茫,山石结构的脉络清晰,疏林清旷,天地寥廓。

画家以古为师,已自上乘,进此当以天地为师。(董其昌)古代大师更为重视师造化,师自然。

李日华《论画》载:黄子久终日在荒山、乱石、丛木、深筱中坐,意态忽忽,人不测其为何,又每往泖中通海处,看急流轰浪,虽风雨骤至、水怪悲诧而不顾。噫!此大痴之笔所以神郁变化几与造化争神奇哉。


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。”
崂山给我带来无穷的画卷。画家面对景色无尽的大自然,要用心去品味、阅读、探究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
我又想到了清代石涛“黄山是我师。我是黄山友。”的名句,如果大师不对黄山痴迷,岂有此句。来到崂山,往往眼前天开画境,胸襟顿开。


其实,每一次写生的过程都是在一次次一遍遍用心阅读崂山,我才刚刚翻开这部巨著长篇的第一页。